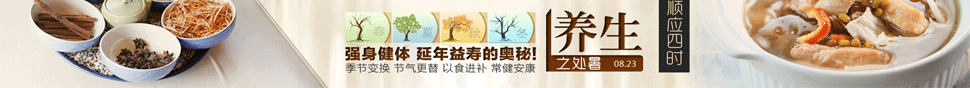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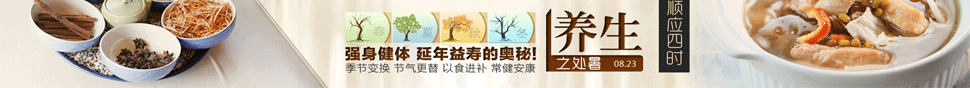
中学生容易模仿的哲理记叙文精选(九篇)
挑水浇石头
王清铭
向晚的炊烟纷纷抚摸天空的时候,老祖母已经做好晚饭,端着一小畚箕的草木灰,走在夕晖中。
家乡的山叫“西山”,却是在村子的南边。祖母在西山的榛莽中刚开垦了一块地,长,一把扁担;宽,半把扁担。祖母往南走时,路上碰见村里人,就打了招呼,村里人问她去哪儿,她往山那边一指,说:“‘挑水浇石头’去。”
村里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她的意思,笑了。祖母也笑了,脸颊上飞起两朵红晕,不知道是兴奋,还是被夕晖染红了。
我当时刚上一年级,听到老祖母的话很纳闷:她又不用水桶挑水,那块刚开的地都是沙土和黄土,哪来的石头?我问祖母,她说,你长大后就明白了。
祖母六十多岁,长年沉重的劳作压垮了身体,右腿已经跛了。她蹒跚着往前走,肩上的天空一高一低。
我拿出作业本,开始写课堂上老师刚教的数字。村里没有幼儿园,我们小学的启蒙就从写数字开始。“1”好写,我很快就写满一页;写“2”时,我怎么也写不好。姐姐手把手教了好多遍,我自己写时,还是把她说的“曲项向天歌”的“鹅”写成了在泥土里钻行的“蚯蚓”。姐姐有点生气了,对我说:“你怎么这么笨?我真是‘挑水浇石头’。”
我羞愧地低下头,明白姐姐话中的意思,“挑水浇石头”,就是一点用处都没有。
祖母回家了,刚好听到姐姐的话,就对我们说:“挑水浇石头,不是没用,最少还能浇出一些苔藓。”
我脑中闪现阴雨绵绵春天的情景,连续下了很多天的雨,门前的石板和石条冒出了一些绿意,那就是苔藓。原来石头也有自己的春天。
我一下子明白了祖母的意思,她在说:有些事看起来毫无用处,但坚持时间长了,也会有收获。
我又开始写数字了,虽然依旧写不好,但我似乎看见了“石头上的苔藓”,有了信心。
祖母的那块地,种植了木薯,木薯耐旱,在贫瘠的土地上依旧长势旺盛。祖母依旧经常“挑水浇石头”,把煮饭后灶膛里的草木灰掏出,拿到那块地。在乡下,“死灰复燃”有另一种特殊的方式,就是化为庄稼的肥料。后来,这块地种了花生、地瓜等。祖母挑水浇的“石头”,不仅长出“苔藓”,还开出了乡村里一朵美丽的“野花”。
读中学时,读明代宋濂的《送东阳马生序》,文中有一句话“媵人持汤沃灌,以衾拥覆”。“沃”就是浇,跟我们本地话的读音和用法一样。挑水浇石头,按我们的本地话读,就是“挑水‘沃’石头”。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了祖母的那一小块地,她看似做了无用功,但努力并没有白费,贫瘠的土地也逐渐肥“沃”了。祖母的这句土得掉渣的格言也“肥沃”了我的生命。
我参加工作后,痴迷于文学创作,写了很多文章,都没有发表。坚持不下去的时候,我想起了老祖母的话:“挑水浇石头,最少还能浇出一些苔藓。”于是我又有了信心。后来,我汗水浇出的“石头”长了“苔藓”,还开出了“花”。
冷是孬种
王清铭
屋外的寒风像蹲在屋角的小狗一样狂吠,起初是一只,后来村里的狗都叫了。寒风呼啸。
我们看着屋顶,那些原先透进月光和星光的天窗黑漆漆的,与黑色的瓦片没有分别。瓦楞上寒风捏细嗓子在叫,风太大,冻得整个屋檐似乎也瑟瑟发抖。
房屋没有毛孔,不像我们,恨不得每个毛孔都闭合起来。冷得像铁的小手往袖管里插,我们尽量弓着身子,缩小暴露在外的身体,似乎冷也有重量,我们都咬着牙关驮着。
一盏煤油灯,顶高了空中压下来的漆黑夜色。老祖母看着我们发抖的样子,笑了。她挺了挺早已佝偻的背脊,对我们说:冷是孬种,你一硬,它就软了。
看着我们几个小孩子茫然的表情,祖母又说:不信,你们挺直腰杆,就不冷了。
我们听祖母的话,挺直了腰杆。奇怪?怎么没那么冷了?
一阵寒风拂过后,煤油灯的灯芯微微俯身,而后又挺起,仰面向上。灯光亮了一些,逼近的夜色也后退了一些。
祖母说,你们手脚用力抖一抖。我们就摆动自己的手和脚,不一会儿,一股暖流从四肢开始漫向腰部、胸部,最后流遍了全身。煤油灯黯淡的光线也温暖了,仿佛是一缕一缕的阳光。
我们很惊讶,这冷怎么就被我们甩掉了,像邻居的那头水牛甩掉牛脖子上的牛虻?
祖母又说,你们喊一喊,喊了就不冷了。
我们先是咿呀地喊几声,觉得声音太单调,有人就唱起了乡村童谣。童谣是循环往复的,我们就一直如村里的老唱片机一样唱着,祖母也跟着我们哼唱。
“一根竹扁水面浮,阿公叫我去牵牛。……”我们的思绪也随着竹片在水里漂浮,一直漂到很远的地方。我看到每个人的眼中都有一点光,这光是煤油灯照射的,也是自己闪射的。
冷很像收割季节稻田上空飞来的麻雀,刚停在沟垄上,我们喊几声,它们就吓得扑棱翅膀,飞得远远的。农人在稻田里插一个稻草人,也吓得麻雀逃之夭夭。
母亲早已给我们的床铺加了一层稻草编成的草垫,稻草垫是祖母在秋天时早就编好的。我们躺在床上时,感觉就像在稻草垛上,嗅到了谷子的味道和稻草上残留的阳光的味道。我们梦见了稻田、阳光和小鸟,一睁眼,屋顶天窗落下早晨橙红的阳光。
儿时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,早晨到处都是白霜。四季苍翠的龙眼树,耐不了寒冷,叶子枯干了。在南方,没有火炕等保暖措施,我们靠祖母说的保暖方法穿越隆冬。祖母说,冷是孬种。我们就挺直腰,用自己的歌声将冷赶走,动手动脚将冷赶走。
几十年过去了,又到了寒风凛冽的冬夜。现在有保暖性能很好的衣服,我不怎么感觉冷了。夜深了,我手脚有点冻,突然想起老祖母说过的御寒方法,就像儿时一样重复了一遍,果然身上有些暖。
祖母是个文盲,说不出驱寒的道理,但她说的方法朴实而深刻:抖抖手脚,这是运动驱寒;唱唱童谣,这是转移注意力;而腰杆挺直,这是增强自己的信心和意志。有了坚强的意志和科学的方法,冷这一孬种自然就逃离了。
“冷是孬种,你一硬,它就软了。”我耳畔回响着老祖母穿透岁月风尘的声音,突然想:何止是冷呢?许多的困难险阻都是孬种,我们挺直腰杆,它们就软了。
雪化了是水
文丨王清铭
学生高中毕业前的最后一节课,我一般都要出一个看似简单通俗的问题:雪化了是什么?
学生不加思索,异口同声回答:是春天!
我神色凝重,手一摆,压低声调说:不对。
学生小声嘀咕,互相诧异的眼神。我用威严的目光使他们安静下来。
“雪化了是春天,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答案,但它是现成的。你们脱口而答,说明未经自己的思索。诗意是别人体会的,答案是误人的。你们没有带自己的脑子来。”
乡村雪景来源:互联网
学生面面相觑,有几个同学想站起来反驳。我将手往下一压,继续说:
“也许你们觉得老师在给你们泼冷水,但应该知道,水虽冷,但至少还未结冰,天气还没有到朔风凛冽的程度,你们都没有进入‘冬季’的思想准备。”
我停顿一下,举手并往上呵气。有些学生大概想到冬天的寒风砭骨,不禁打了一个哆嗦。
“真正的寒冷冬天,是呵气成霜的季节。你们跟我一样,都没有看过雪,只从课本间接体验岑参所写的诗句,‘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’,你们就以为雪就象绽放的美丽的梨花一样。知道一个冻僵的人应该怎么救治吗?”
学生生活经验有限,有人迟疑一下,低声回答:穿棉衣,用暖水泡。
“你们错了,”我斩截地说,“一个人冻僵了,需要以寒制寒,用雪擦拭他,让他慢慢回暖。”
学生睁大了眼睛。“就像你们不知道雪一样,在走进社会前,大家都为自己设计好花朵一样美丽的前景,但是——”
学生似乎联想到社会生活的艰辛,不自觉低了头。
“夜深知雪重,时闻折竹声。雪是具有破坏性的,能让坚韧的竹子折断。在冬天来临时,你们要做好防寒防冻的准备。衣服要暖和,还要给自己的心灵保温。柴门闻犬吠——”
学生很整齐地读出下句:风雪夜归人。我赞许地点点头。
“是的,你们也许要在现实中不断奔波,做一个风雪夜归人,所以你们不要耽于雪化了是春天的梦想。”
我放慢语速:“雪化了,说明天气回暖,但离春天还有一段历程。即使是初春,也还有春寒料峭的时候,不做好御寒的准备,你们不流泪,也会大把大把的流鼻涕——因为你们都感冒了。”
学生哄堂大笑。“现实是残酷的,它会迫使你放弃许多的诗意和梦想。也许你们将是孤独的,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但在逆境中,不要冷漠,让激情的血冷却。”
我眼前仿佛出现了柳宗元的《江雪》图,声音陡地昂扬:“人生的孤舟上,你们是那位身穿蓑衣头戴斗笠的渔翁,你们要记得带一颗心,独钓寒江雪!”
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,我知道,这掌声不只是给我的。
点亮一盏灯
文丨王清铭
黄昏时我依旧到后山跑步,已是秋天了,天暗得早。我跑了很长距离,到旧池塘时,已强弩之末。天冷了,但汗水仍然涔涔流下,腿部肌肉酸痛,有点抬不起腿了。这时,耳畔传来一阵稚嫩而又清脆的歌声,仿佛沾满露珠的树叶,在寒风中摇曳。我未及分辨声音来自何方,脚步突然轻快了,歌声似乎转换为我的力量,又似乎延伸出一条向前的道路,我的疲惫随汗水流失了。
当我环山麓奔跑的时候,才发现唱歌的孩子。他只有十一二岁吧,手里拿着歌谱,在母亲的指导下,正在练歌。他们太投入了,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快步跑过的身影,我也没有去打扰他们,我跑过他们的时候,脚步更加强劲有力。
从山脚下绕回来的时候,他们已经走回旧池塘了。我又跑过了一路歌唱的他们,这次我回头对那个孩子说:“你唱得真好,听了我跑步都有劲了。”他的母亲很高兴地向我表示感谢。
其实要感谢的倒是我,是他们的歌声驱散了我的疲惫,带给我活力和愉悦。他们不是为我而歌唱的,但却在无意中给我力量。
我们比较在意那些为我们做事、给我们帮助的人,但往往忽略那些无意中让我们受益的人和事。对赠送玫瑰的人,我们会表示感谢;对那些种植玫瑰给我们芬芳的人,我们常常忘了表示谢意。他们不是为我们种植的,但他们的玫瑰无意中给了我们美丽和芬芳,如果我们领悟到这一点,就会明白,这世界并不缺乏爱,只要你能清楚爱也有两种:狭义的和广义的。广义的爱没有具体的施与对象,但它也能让很多人受益,比如种植玫瑰的园丁,比如我路上碰到那个唱歌的孩子。
有一个作家感慨说:“很多人会看到月亮之美,都不会感谢邻居门口的灯以及屋后棚栏上生动的牵牛花。”少年时,我生活的乡村终于通上电,那时大家都还很贫困,灯开得少,灯泡尽量换亮度小的。最亮的灯是自家门前悬挂的路灯,到夜里每家每户几乎都开着,如果不是到夜深大家去睡觉,路灯很少有熄灭的。多年以后,我才明白,当时村里没有路灯,道路又不好走,大家开着门前的灯,不是为了给自己照明,而是给路过的人一点光明。节俭的他们不怕浪费。纯朴的乡人根本就没有特意为别人亮着灯,但他们模糊地觉得,开着灯总是对别人有用的,于是灯就亮着。村人在村里泥泞的道路上走着,也不用带手电筒的。
多年以后,我回老家,走在水泥道上,看到电杆上明亮的灯光撒在地面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想起以前读过的巴金的《灯》,印象比较深的是这样的语句:“他们点灯不是为我,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。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。”“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,可是连我也分到了它们的一点恩泽——一点光,一点热。”村人拉亮了门前的灯不是为了我,但我确实也分到了它们的一点光和热。
或许如以前的村人一样,我们多想着别人,我们就会在无意中为别人点一盏灯。这个世界上,这样的灯多了,就会璀璨一片。我们也不须着意去做一些善事,只要有善意,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盏明亮的灯。
富翁的哲学
王清铭
富翁长得很不起眼,跟我站在一起,别人都会把他看作我的跟随。当然,我也不起眼,走在日渐繁华的街道,高楼明亮的马赛克一照,感觉自己就象街上随处可见的三轮车车夫。
小城里的三轮车很多,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红篷车,专门用来载短程的旅客。从业的人员多是城郊被不断“发福”的县城挤占了土地的农民。他们谋生手段少,只能用体力和汗水来换取菲薄的收入贴补家用。一天一二十元,一月下来五六百元,比最低生活保障线高些。营业的人多,车费自然便宜,一般在二三里一二元这区间徘徊。
我出身农门,对这些车夫多少有点自发的同情,付车费时一般往高的掏,也就是说,可付一元或一块五的,我选择后者。富翁却不,一定选最低价,不顾车夫的白眼扬长而去。顺便交代一下,富翁是我高中同学,毕业后我考上大学参加工作,到现在还是穷人;富翁考不上大学,却成为名副其实的富翁。想到这些,我心里的PH值总是低于7。不过,我觉得富翁很小气,有点为富不仁的味道,一位身家几千万的人,弯一下腰都能赚个千八百的,还会去计较区区的五毛钱?
因为同学聚会,我与富翁有两次同乘一轮红篷车的经历。富翁倒善体人意,不驾驶家里的“宝马”,让我们这些把自行车当专用车的穷人自惭形秽。下车时,富翁把付钱的机会慷慨地留给我。三里多的路程,价位在1.5—2元,我掏了2元,并无找零钱的打算。富翁倒很认真,伸手向车主要那5毛钱,当时我有点嗤之以鼻。
车主不情愿从口袋中掏出一张脏巴巴的小钱,年轻气盛的他扔下一句话:坐不起三轮车,就别显摆!富翁一笑,我看见他的笑容一点苦涩。
同学聚会无非是说说话,发发牢骚,喝喝酒。席间富翁给我讲起了自己的经历。
高中毕业后,家境贫寒的他为了养活自己,到县城擦皮鞋,一天赚几元前,虽脏点累点,但衣食无忧,他过得很自足。富翁很精明,擦一双皮鞋3—5毛钱,富翁让顾客随意付,多数人会付5毛。擦皮鞋在这里是低*的职业,人们处于朴素的同情或心理优越,一般都会往高的付钱。富翁多了一份额外的收入,这一段日子他过得很滋润,用多出的钱买点劣质白酒,陶然醉一回。
富翁说,如果我多给车夫5毛钱,他们有了这额外的收入,也会象年轻时的他一样,喝一点劣质白酒陶醉一回,让生活的激情慢慢被这点小满足沤烂。
富翁命运改变是在遇到一位经常来摊前擦皮鞋的商人。商人每次擦鞋,雷打不动地给他最低的3毛钱,有一次富翁没有零票,一般人不会在乎,商人却不,非要他去换零钱。年轻气盛的富翁象那个车夫一样抢白商人。商人不生气,反而坐下来注视他,说,你这么年轻,就为这2毛钱生气?人生很长,你该为自己生气!
富翁说当时自己僵立在那里。良久,他将皮鞋摊砸了,决定去闯荡一番。富翁成为富翁还有很多曲折的经历,富翁不说,我也不想去问,有这个故事就够了。
富翁说,有时候人的同情心反而害了一个人,特别是年轻人。如果不是那个商人,说不定他现在还在县城的某个旮旯擦皮鞋呢。
人一般要到绝境的时候才迸发最大的能量。不是我们不思进取,生活中的一点小满足经常使我们的斗志懈怠,我,还有那个年轻的车夫何尝不是这样呢?
富翁其实很慷慨,福利院每年都收到他大量的捐款。
天亮从自家天窗开始
王清铭
我的老祖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俗语:“天亮从自家天窗开始。”老家的老屋是土木结构,少时没有闹钟,我们看时间,就是躺在床上看天窗。天亮了,太阳升起了,都是从天窗看到的。在天窗,天亮是一片白,太阳升起,是一片红。但我念书多年以后,还弄不明白老祖母话里的意思,一直很纳闷,我掌握了那么多的知识,怎么就弄不清文盲的祖母的一句话?
我住的是单位的宿舍,没有专门清理卫生的人。有一次,我洒扫门前,又顺着楼梯扫到下层的大门口。我突然想起了文盲的祖母的这句话:“天亮从自家天窗开始。”
少时跟祖母一起去田野除草,祖母总是把杂草收拾好,捆扎带回家。附近的田垄上,邻居一般都是把草放在那里晒干后,才收回去的。我看到,偶尔经过的村人都是小心翼翼地从草上踩过,生怕自己滑到。他们经过我们田地的时候,就没有那样的警惕了。我问祖母,她没有回答。
村里通了电,村人怕花费多,用电很节省。我们从门前空地晒凉回家时,一般都顺手把门前的灯熄灭。一贯节省的祖母经常又拉亮这两盏已经熄灭的灯。我们问她,她只说:“可能还有过路的人。”
以前门前的道路都浸满泥泞,凹凸不平的。晴天的时候,祖母总是用锄头将坎坷磨平,下雨时,她在门前垫几个瓦片。我问祖母,她只是回答:“为过路的人走得顺畅些。”
没有文化的祖母说不出道道,但在我清扫完门前之后才明白,要保持一幢楼的洁净,先就得从打扫自家门前开始。“各家自扫门前雪,莫管他人瓦上霜。”如果每个人把自己门前的雪和瓦上霜清除干净了,那么所在的环境自然一片天朗气清。
天亮从自家天窗开始。我不知道这句话说的是否就是一切从自己做起,我想找老祖母求证,但她早已不在人世了。过了不久,我们单位发布告说,为了宿舍的洁净,请保持门前的洁净。
在祖母去世前后,我经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,但我没有颓丧。在老家的时候,我所看到的第一眼光明就是从自家的天窗开始的,偶尔我会想到祖母的话,并将天窗里看到的光明收入自己的心中。后来我挣扎着走出了人生最黑暗的时期,没有别人的帮助。我想起在老家的经历和老祖母的话:天亮从自家天窗开始。
我一直忘不了在老家看天光的情景,的确,最早看见天亮的是自家的天窗。多年以后,我才明白,祖母的话里有两种意思:要给别人无私的帮助;能帮助自己的只能是你自己。
(图片均来自网络,致谢!)
年福建省中考
作文题目为
《最好的作品》
成长的路上,我们不断迎接挑战,努力完成各式各样的作品,这些作品或有形,或无形,都是我们成长的印迹,也许其中就有自己心中最好的作品,也许最好的作品还在追寻的路上。
以上文字给你什么样的联想和感悟,请以“最好的作品”为题,写一篇记叙文或议论文。
(以上内容根据考生口述整理,具体内容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为准)
最好的作品
王清铭
夕阳被门前树枝枯瘦的手扔进西边的山后边,之后,溅起了一地的夕晖,零散的归鸟啼鸣,以及几声鸡鸣狗吠。
我拿出一截木薯秸秆,站在家门口,立刻被泼上一小木勺的夕晖,感觉自己也亮了。木薯秸秆,心掏空了,上面用小刀挖了几个“笛孔”,木薯秆的一端,蒙上一层从哥哥作业本撕下的纸。用来粘贴的浆糊是剩饭的米粒。
我们当过牧童,但乡村没有诗意的短笛。不甘寂寞的我,就用自己的方法制造声音,挖了孔的木薯秆就是我的短笛。我学莆仙戏台后台的乐师,深深吸了一口气,短笛横吹。吹一声,是鸡鸣;再吹一声,是狗吠。如此反复,我有点急了。笛子不响,就用嘴巴制造音乐。“呜……”我的“笛音”是乡村唯一的童谣。
“一根竹扁水面浮,
阿公叫我去牵牛。……”
童谣咏唱的是乡村孩子重复而无休止的劳动生活,我一遍又一遍地“吹奏”着,家门口远处的小溪似乎涨水了,反射过来的波光由橙红色变成灰黄色,而后是灰白色、黑色,天黑了。
恍惚间我听到一声叹息,放下短笛,耳畔只有晚风吹过门前苦楝树叶子的声音。苦楝树正在开紫色的花,像一种我说不出的忧郁。
天色比脸色更黧黑的时候,父亲从村里的陶器厂回来了。父亲和村里的男人们一样,除了土里刨食,都是村里陶器厂里的工人。他善于拿捏泥土,做水瓮(水缸)的技术是一流的。我爷爷是陶工,父亲自然也是陶工,十二岁时就开始做陶器,帮爷爷养家了。如果没有发生意外,我将来也是陶工,像父亲一样。
为了生存,爷爷从邻村搬进了新窑村。父亲拆了爷爷盘下的旧房子,建了新房子。新房是泥土夯筑的,有青黛,没白墙,土墙就裸露着,像父亲经常光着的上身,青筋毕露的。父亲回家后,泡一杯劣质的茶,搬一张竹椅子,坐在家门前抽自卷的劣质纸烟。他猛吸一口烟,烟头就在夜空中炙了一个小洞。烟雾在他头顶环绕,他有时顺便打量一眼新房子,在夜色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
那一年,我七岁,父亲四十岁。我现在称为老屋的那座新房子刚三岁。
父亲抽一口烟,对我说,笛子要用竹子做。我想起门后几根竹子。父亲说,这边、那边挖一些孔,九个孔。一孔蒙笛膜,一孔用来吹,剩下的七个孔就是七种声音。我看看夜空,寻找北斗七星。我想象着,我即将做成的竹笛会吹奏出北斗那样明亮的声音。
哥哥有一把铁片磨成的小刀,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拿着它蘸着水,在门前石条上磨。父母早去田里劳动了,天很快就被我磨亮了。从门后拿一根竹子,用菜刀砍下一截后,我再用铁片刀在上面挖孔。竹子很坚韧,风雨都不能折断它,一把小刀又奈它何?我左手攥紧竹子,右手加大用刀的力度。竹子不甘心受摆布,一滑,化我的力道于无形中。我与竹子对抗的最终结果是,我右手握着的刀,全部划近我左手的大拇指。眼前飘过一道红光,我还以为是早起的太阳反射过来的光。
家里没有其他人,我怕父母责怪,就想方设法止血。先抹一种叶子像小勺子的草,无效;听说唾沫能止血,我大口大口地往上面吐,无效;用水洗,更无效。……我当时更关心的不是血呼啦啦地流了多少,而是赶快止血,不让父母知道。不知过了多久,大拇指的血流光了,血止住了。
快中午时,父母从田地劳作回家,才发现我受伤了,带我去赤脚医生那边包扎,或许是巧合吧,缝了七针,跟放出音乐的笛孔数目相同。
那一根沾满鲜血的“笛子”,不知道放哪里去了。
我手上的疤痕还在,好了伤疤忘了疼,我也很久没有想起那把“笛子”了。这把“笛子”,或许是我手工史上最失败的“作品”了,但我最难以忘怀的是儿时对笛孔的想象,那把我在想象中制作完成的笛子,能够吹奏出星星一般明亮的音乐。这贫乏乡村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想象,或许就是我曾经留下的最好作品吧?它远比我发表的一百多万字的文章珍贵。
前几天回老家,父母还住在他们年轻时建的房子里。家,也变成了老家;新房,早变成了老屋。老屋也四十多岁了,老了。
这一年,父亲八十多岁。今夜我站在高楼上往窗外眺望,街上霓虹灯闪烁,天空没有一颗星。看见久违的天空,我突然想起,我很久没见的北斗七星,曾经如想象中的笛孔,流淌明亮的笛音,已经四十多年了。
作者简介:王清铭,笔名应鸣。全国中高考语文热点作家,某县作家协会副主席,县政协委员,中学高级教师。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读者》、《青年文摘》、《意林》等发表散文多万字,诗歌五百多首,已出版个人散文集《半瓶阳光》等四部作品。作品入选《大学语文》等大中专教材、香港语文课本和中小学语文教材等。近一百篇散文被编为中考、高考现代文阅读题(包括模拟题)。
十篇散文被编为全国各地市中考阅读题。《生活如椅子》《春天里种植自己》《与父亲抬担子》《半瓶阳光》《阳光的疤痕》等被编为佛山市、威海市、常州市、河池市、衡阳市、恩施市、新疆区等中考阅读题。
第一次下水写中考作文题。
欢迎广大学子来仙游金石中学就读!王清铭老师写高考全国一卷作文丨管仲:不以一眚掩大德
高考记忆丨考场外的蝉鸣,高考是人生的第一次蝉蜕……
高三语文最后一课丨相信未来,相信自己!
高考作文丨用心理学效应增加作文说理分析的深度(独家)
届高考散文阅读名家作品精练:王清铭专练
当高考遇上端阳丨文化随笔:端午节随想
高考冲刺丨漫画作文:娱乐越来越多,思考越来越少
这两篇写父亲的文章,应该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……
乡下父亲们没有父亲节(组诗)
每个人都是萤火虫——王清铭杂文选(五篇)
一篇《与父亲抬担子》学会记叙文的细节描写和结构技巧(附朗读)
儿童节丨这些年我写过的童心和诗(五篇附朗读)
王清铭老师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bianxua.com/pxyf/6629.html


